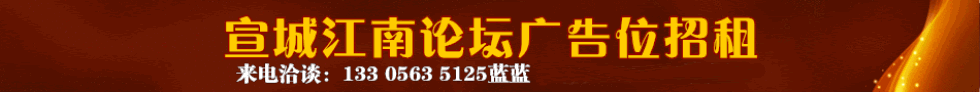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本帖最后由 大漠流沙 于 2024-7-19 05:59 编辑
飘在云端里的烟村人家,从刀耕火种岁月,便把祖先的根写在骨子里,生就的山旮旯的乡音,写就了土生土长的倔犟,如同村中那棵老槐树,生来就是那种倔像。山后一泄千尺的瀑布,把山村打理成一帘幽梦,环境清新如画。小溪穿村而过,常年鸣唱在街心,汩汩潺潺,女人们早起,就操起洗衣的棒槌,声此起彼伏,敲打着衣服里的龌龊,哼着山野的摇篮曲,喋喋不休地唱着妹妹爱情郎。男人们看着那些挑逗的娘娘腔,便歪着脖子吼起了油锤撞木榨的高昂。女人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们喜欢雄性的粗犷,看那裸露的皮肤油光发亮,在大自然的阳光下,晒得熏黑流光,她们看中的便是山乡男子汉的淋漓与酣畅。阳光的老辣,怎抵得男人们皮肤的倔犟,那是揉面一样揉成的琥珀之光,这就是故乡人终生炼丹一样练成的功夫与沧桑。盛夏,我常常随夏风回山乡,看看众乡邻里,瞅瞅老碓屋旧磨房,找几枚土鸡蛋,做个蛋炒韭菜黄,邀几个儿时的老伙伴,喝上二两老白干,猜上几拳。空了,再爬上那一览众山小,拍几张山乡速写,寄去远方,给某报社或某杂志,填空补缺,成就一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