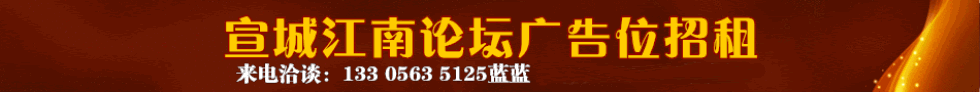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发表于 2023-8-12 22:00:5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3-8-12 22:00:5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安徽合肥
珠城岁月(八)
照通常说法,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一条明显的地理分界线,尤其在气候方面表现突出。蚌市虽在淮河南沿,但气候明显呈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多风沙乃是这儿的显著特色。刚去那会儿眼睛发涩、口干舌燥、嘴唇开裂,令南方去的人很不适应。晾在室外的衣服待收回时已是一层灰沙。人走在路上,时不时就会有一阵呛人的灰沙兜头袭来,让人眼都睁不开。
那时,经常召开全市规模的群众大会或教育系统的师生大会,其内容不外是是什么庆祝活动。每当各校师生排着长队往市体育场集中时,回头看我们学校队伍的人脸色大多较白,这是因为我们校至少有一半人来自南方。再看中学或其他学校的学生,脸色则明显较黑,这种长期受北方干燥气候和风沙熏陶所产生的作用在人的外貌上也得以显现。
我们这一届毕业时共有12人留校,女7男5。章生余、邹晓牛(后改为邹哓),我们3人被学校分配在东院一座小黄楼二楼上两间连通的木地板房间里。刚开始在学校食堂吃饭,我们3人的饭、菜票是混在一起的。后来章调回老家,邹与徐桂芸(我们下一届留校)恋爱,我们这3人小团体遂告解体。
3人经常借了自行车到处玩,学会摄影后经常外出照相并自行洗印、放大黑白照片。还到他俩原先不认识的在锅炉厂上班的徽州(那时宁国、旌德、绩溪都属徽州地区)老乡家吃饭。有时顺淮河大堤骑车骑了好远才返回。
说到徽州老乡,其老乡观念深重非他地人可比。他俩这个老乡就是有一次在街上偶尔听到他俩的乡音主动搭讪后结交的。此外,在我们上学期间,我们排的几位排、班干部正在开会。此时有别的排的徽州同学来找正在开会的一位老乡出去玩。我们这位徽州毫不犹豫地对王元贞排长:老乡找我去玩,我请个假。看在老乡们关系如此亲密的份上,排长当即爽快地允准,你去吧。看着一行人离去的身影,在座的人无不为徽州老乡的深厚情谊感叹之至。
来上学前,留校的12人中,章在老家旌德的公社做过事,邹自旌德出外当过兵,其他都为下放或回乡(家在农村)知青。
初始参加工作,我们每月只有22.5元(其中0.5元为商品粮食补差)。如果每月按15元伙食费,一个人单独在食堂吃饭则紧紧巴巴。而3个人共45元伙食费,吃的菜品就要丰富得多。
那时我们那点在今天看来少得可怜的工资(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两千多元)与学校的教授们比,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那时学校的4位四级教授其月工资为196元。这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其中留美的贺治仁教授(江西籍,贺子珍族内兄弟),曾于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昆明)经济学系(商学系)任教。在安财曾有人好奇地问他有多少存款?回说10几万,这让人吓一跳。难怪有人觉得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条件特好。有的据说还家藏金蛋(黄金铸成)。他们不但手戴常人难得一见的名表,还在桌上、墙壁、屋角等处都置有大小不一的闹钟,小小的客厅里还有平常人家当时没有的沙发。
这位贺教授老夫妇俩常请我们去吃饭,视我们如同儿子。有时我没钱用了就向他们借,贺妈妈说,你若一次还不了就分次还。有时实在没钱时我就拿一、两件旧衣服到调剂店里换个兩三元钱以补不足。
贺教授有一次带学生在工厂实习,听厂里人喊某人为马教授。他很好奇,厂里也有教授?经向他人打听,得知这位“马教授”知识渊博。于是主动与之打招呼,二人相谈甚欢。
贺教授回校后感慨地对我们说:这个“马教授”不简单,连马克思的夫人名叫“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他都知道,我原先还不知道呢。
当时还有个教师陈有钦虽非教授,但月工资却有220元。听别人介绍才知,早些年,学校要开办外贸专业,就到上海外贸局商调人员。对方出示了这陈的档案,校方经办人一看,此人月工资仅22元,便宜,当即拍板。回来后才知是220元,原来少看了一个零。此事被当作笑话经年流传,后来此专业却多年未开,他也只能在教育组(教务处)从事行政工作直至退休回上海静安区愚园路家中。
陈解放前在上海工部局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供职,小提琴拉得很好,于是业余时间就教(那时不收费)小青年们拉小提琴,当时校内外有许多他的学生。
还有一位5级教授(月工资160多元,再下来高教6级就是副教授与讲师最高级的交叉级)临退休前,对同事们说,以后你们到上海我请你们吃饭。后来有一次,真有人出差顺便去了他家,然而到吃饭时就是不见动静,12点多了,主人才说,我请你们吃冰淇淋吧。客人们无不诧异至极,看架势,估计其虽为主人在家中却作不了主。只好说不了,遂扫兴退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