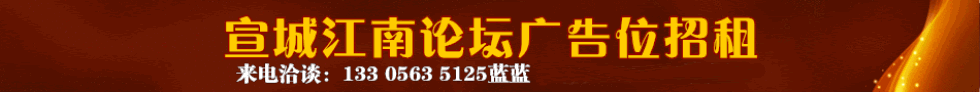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曾经的白湖(续五)
梅山小学
五十年代末刚到白湖时,农场尚无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与前面的学兄学姐们一样,我们这些场部或一大队小孩子多数由家长们送往白湖南边约两三华里的梅山小学读书。
9月份的一天,父亲与他的同事们将各自从外地学校转来的孩子们送到当地的这所农村小学。
这好像是所由过去大户人家的房子或祠堂改建的小学。学校院子座北朝南,一进院门,是个很大的院落,迎门是一座带中堂的二层小楼,房子已很老旧。后来知道,东、西两边二楼分别是人睡在地板上的住校男、女生宿舍;底层中堂两侧全为老师办公室;东、西两侧各有走廊(廊柱下皆有石柱础)的厢房为教室;在院子东北角是食堂,此处有一侧门通往院外(另有教室在院外东侧的平房里,平房与院子之间是兼作篮球场的运动场)。
那天,趁家长们与老师办理我们入学手续之时,我透过一扇开着的门对一间教室里望进去,只见由两根木棍支撑的黑板似倒非倒地靠在墙面已斑驳落离的山墙上;学生们依在高低不等、有长有方(板凳同样如此)的桌子旁上课(后来知道这些千差万别的桌凳全是由学生从家里带来,当每届学生六年级高小毕业时,其所带桌凳即各自带走)。看到这条件与我老家上的小学如此天壤之别,顿时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办完手续,我被班主任语文宛老师带进三年级教室。我没有自己的桌凳,只能勉强挤在同学的一小截凳头上,挨着一小点桌角上课。
手抄课本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的语文、算术课本与这儿的不一样。我的是上教版,他们的是人教版。暂且只能与同位同学合看一本书。
为解决这一难题,父亲让他负责的大队门诊室的一位舒城籍年轻医生替我手抄。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借了同学课本回家,让解医生手抄。经连续三四个晚上的辛苦工作,两本字迹工整绢秀、装帧甚为美观的课本“出版”了,我喜出望外,直到现在我一直忘不了那位曾是解放军军医的解医生。可惜的是,1969年夏天发大水,所有家属被转移至场部西面的公安部队团部,而我的从小学一年级起的所有课本都未及带走。一个多月左右待水退回来时,包括手抄本在内的课本全被好抽烟的人卷烟抽了。
劳动课
那时学校有农忙假。平时则时常组织三年级以上(一、二年级小朋友则在收过的田地里捡掉落的稻穗、麦穗、黄豆、蚕豆等)的师生们在学校菜地或到附近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凡插秧、割稻、割麦、割油菜、拔黄豆、拔花生、拾棉花、插山芋、种南瓜、种菜等一应力所能及的农活都干了个遍。
第一次用锯镰刀(我们老家只有L形的长木把镰刀)割油菜,由于没经验,加之油菜棵长得密匝,刀插进菜棵后看不见具体位置。当我左手抓一大把菜棵,半蹲着用右手持刀对粗壮的菜杆猛力一拉,顿觉左手指一阵剧痛。赶紧抽手出来,只见左手无名指指尖背部带指甲被拉开一个口子,血流如注。老师用一手帕将我手指扎紧,让我捂紧赶紧回家。好在那块油菜地就在梅山北侧与庐无公路之间,离位于公路北侧的一大队不远,很快到门诊室让医生作了处理。至今无名指指甲上割痕仍清晰可见。
算术老师
我们的算术老师也是学校教导主任,姓徐。每次上课前,凡完成得好的作业本皆由课代表提前领回发给各人。开始上课了,徐主任手捧教本、备课笔记及少量留下的作业本走上讲台。他先拿起一作业本,对着上面的名字大声喊:某某人站起来!接着针对作业本上的错误对着这学生大声呵斥!看你做的什么鬼东西!并越说越气。对那些错误特严重的,则边发火边将作业本撕成碎片,砸在该生身上。
有时上课前,小朋友们正在教室门外疯。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会突然指着人群喊:来来来,过来考试。小朋友们吓得一窝蜂躲进教室关上门。只见他气呼呼的推门走进来,拉上某一个他觉得不顺眼(平时成绩不好)的到办公室去临时做算术题。有一次我同位那个19岁的史姓男生上课前被拉去回来后,心情显得特别沉重。果然上课后徐主任将他狠训了一通才罢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