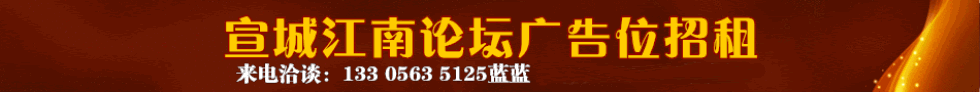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发表于 2024-11-6 22:49:1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4-11-6 22:49:1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安徽合肥
另一类白湖人
五十年代末刚到白湖时,只听大人们说,三类人员是坏人,千万不要与他们接触,不然会有危险。
对于大人们所在意的事,作为小孩子听过就丢到了脑后。
刚到一大队不久,常见三类人员被大批调入或调出。其时庐(江)无(为)公路上往往数十辆六轮卡车排了很长一列。
当他们被集中坐在空地上由管教干部训话或被调动行走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则在他们中间或周边跑来窜去。觉得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根本不像坏人。
当他们在管教干部带领和胸挎五O式冲锋枪的公安战士监督下开始筑东大圩时,常有胶轮板车或其它工具需修理。在我们住的草房边有两间独立草房,里面有一人专门负责修理板车等。星期天或放学后,我们就去那里面玩。至于那人手里有许多各种俢理工具,可我们根本不觉害怕。还根据从一本名为《英雄解放一江山岛》(解放战争)连环画上看到的敌军修建的“土木工事”之说法,将那两间草房也叫成土木工事。
当时的水上运输工具是由他们驾的帆船或小木船;他们赶的三匹马拉的车则负责陆地运输。
当时还有一处可玩的地方就是大队的供应站(最初的供应站只有一间房,主事男的为干部,夫妇俩带一约两三岁男孩住后半间,前半间是木板搭的货架。因为那小男孩走路时鼓凸的两腮一步一抖,所以印象特深刻)。可是那里面吃的东西或小日用品要用钱买,而小孩子身上没钱,去了也白搭。于是土木工事就成了我们如“百草园”般的消遣场所。
后来有了包括诸多工种的杂务队,我们就有了更广阔的玩处。那里有铁工、木工、泥瓦工、篾匠、桶匠、裁缝师傅(因当时没有电和自来水,所以其中的水电工或教授、工程师等因无相应专业可做也只能下大田干活)等。対于他们,我们觉得他们有技术,很能干。
开梅山炸石筑东大圩堤时,他们用木炭、硫磺、硝石自制炸药。每天山上以数片厚篾片叠加作软把的28磅铁锤砸击铁钎的叮当声不断。爆破前,在周边有人警戒,不让行人通过。然后他们在炮眼里填上炸药,点燃引线,接着飞速抓绳攀上安全处躲避。就听在一连串的轰隆声中,大小碎石飞得很高很远。有一次一块小脸盆般的石块砸穿近边一农家草房顶,落在小宝宝的摇床边,令人们大惊失色。
山上采下的大量石块由两人推一辆歪歪车(下坡时人站在车上下溜)在小铁轨上运往工地。
还有一处是供干部及家属吃饭的小伙房(圩子里供三类人员吃饭的叫大伙房(还有供应站、管理员、司务长、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等都沿用部队的叫法)。有空时我们常去那里玩,看他们炒菜或做各种面食的手艺也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我们家有人生病,我按规定去小伙房订一份病号饭(面条)。只见那白案师傅从和面到面条盛碗,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尤其是切面工序,只见他嘴衔香烟,边东张西望地与伙伴们聊天,边两手不停切面。只见厚薄、宽窄一致的面条在一直声的笃笃笃笃声中如流水般从他左手指间淌出,令人咋舌。
还有一处是由我父亲负责的大队门诊室。那里汇聚了十来个各地来的医术颇高的医护人员。我在那看他们给患者治病或聊国内外大事或各种趣闻,获益多多。
门诊室还有一间中药房。整个一面土墙上的小木屉里,盛滿了当归、熟地、桔梗、大黄等数百种中草药(有外购或上黄山等地挖来)。其柜台两侧分别书有“精制饮片、丸散膏丹”字样的对联,象模象样。
他们还将牛骨掺上药物,在大锅里熬成糊状,用竹筷压在方形厚纸片上并使纸片旋转多圈制成正圆形膏药。
门诊室有一位五八年来的时年22岁的王树藩医生。他来时带来好几木箱小说和一直订阅的《人民文学》《萌芽》《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文学杂志,成了我的小图书室。他投向公安厅劳改局《新生报》的稿件每投必中。在1962年前年后,他以参与皖南防治血吸虫病亲身经历,写了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青山红雨》(男女主角分别叫王青山、陈红雨。我看过其初稿)。因其表现不错,他于1963年提前五年(共十年)回家。可能鉴于其身份特殊,其作品后来胎死腹中。
还有原是部队军医的解质如医生因老家有人与其妻有染,他气得要与人家拼命。结果自己反被弄了个十五年。
还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曾不服管教,但他医术高超,常给中青年医生上课。
我初到一大队时,因老家课本与安徽的不同,解医生纯用钢笔连续多个晚上(我放学时借同学课本回家)帮我手抄了《语文》、《算术》两个课本。他也因表现不错,于1963年提前十年回家。以上皆因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后甄别了一部分案件所致。
还有位年轻医生,听说平时不太服管教。1963年夏天时,我看他白汗衫上有“清华大学”字样。可能觉得自己毕业于名校而傲视别人吧。
那位每天在二中队小伙房挣扎着挑水的二十岁上下的男孩,夏夜乘凉时他用纯正的普通话为干部及家属朗诵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里画外音道白或以他嘹亮的男高音演唱当时流行的歌曲。
场部的剧团更是京剧、黄梅、庐剧、泗州戏、歌剧、曲艺、杂技等样样来得。其中一位周姓女演员在来农场前,有一回作为民兵的丈夫打靶回来将步枪靠在门边。她拿起枪开玩笑地对着丈夫说:我打死你。丈夫毫无防备,她扣动了板机。由于剩余子弹未退膛,加之保险未关,终酿惨剧。女的因故失杀人来到白湖。
还有位杨姓女演员,原是武汉某医院护士。因偷他人手表藏在牙膏管里,被发现后也来到白湖,她现学黄梅后来成了这儿的名角。
那个来自南通杂技团的演员表演硬气功时,用铁棍猛击自己头部,竟毫发无损。
有一回来了两个各提一口大皮箱的身着去了标志的军服的人。找到管教干部报到后,即将帽徽、领章等交给干部,然后被带进圩子。
有一回一个三类人员拿钱让我替他在供应站买十个麻饼。供应站营业员觉得我从未去买过吃的且一次买十个,肯定有诈。在她一再追问下,我只好如实告知。她走出门,将躲在门外的那人狠训了一顿。
因他们身上不许放钱,以防逃跑。他们的钱必须交给管教室开大帐。有需要时报干部同意后方可使用。他们的来往信件和包裹,也必须由干部折阅或检查。
有一回一个三类人员将他捡到的一个本子交给干部。上面竟记着谁将来任上海市长,谁任市警察局长等。后来那交本子的人则被立功减刑。
有一次那个种菜园的三类人员让我在塘串河新华书店代买一本《果树园艺学》。可我没买到。
有一个三类人员逃到了佳木斯,并在那娶妻生子,被当地发现后即被抓回还加刑。
1969年发大水时,有逃跑的,由于水太大,无路可逃,只得返回。至于重刑者一般被关在小号子里,有上工者则仍镣铐皆备。
平时他们上工时将饭碗挂在腰上。有人抓到了鳖,即用杂草包上扎紧,糊上烂泥,放进烧土肥堆里,收工时,香气扑鼻的熏鳖即可享用了;有抓到蛇或鳝的,处理好后置于草帽里戴在头上。晚饭时,轻掀草帽,美味即落入稀饭里。
有好烟者还将棉衣里的棉絮抽出,用纸卷上代替香烟。我那两本手抄的课本等就因1969年发大水转移时未带走而被他们拿去卷了香烟的。
曾经的另一类白湖人中五花八门,啥人都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