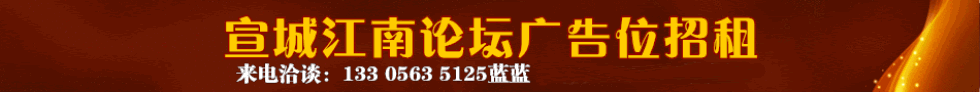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大漠流沙 于 2024-9-21 06:21 编辑
故乡是一幅古典的油画,上世纪的乡村,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把我的故乡定格在记忆里,遥远得似乎遥不可及。篱笆墙与猪狗牛安顿在岁月的那头,我到了新世纪的这头,布谷鸟啼叫的青山绿水间,一望无垠的递田,填满翠绿色的山坳。才脱开裆裤的男子汉,去了不扛枪的军营,在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死了拖了就走”的年代,当兵的不能拿枪,军营里的枪统统都被藏到地下仓库里了。
不抗枪的战士,就只能天天写信,天天盼望着那个叫做风的信使前来叩门,能给送来故乡的消息。有人说,8分钱跑遍天下,可我们的信只盖紫红色的三角戳,一样跑遍天下。被吹淡的记忆,成了折叠的乡愁,父亲来信说,让我请几枚毛主席像章,这个“请”字弄懵了我这个大男孩,不知说的什么意思?更不知是何方神圣让我那古板得再不能古板的父亲,开始了语言革命,说出了我怎么也听不懂的“请”字。 在部队宣传队,我们下乡宣传九大精神,在小溪流淌着浣纱女靓影的田野里,有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乡间小道,坡地里紫色的蚕豆花,和着一片的油菜黄,吞没了年轻的苦恼,蜕变成一抹难忘的夺魂之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如此。年轻的战士,谁都知道“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想家的乡愁,被风迁徙成一个古老的童话,游移在岁月的朝思暮想,落魄在海角天涯的睡梦里,演绎成一生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梦寐,一生的向往与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