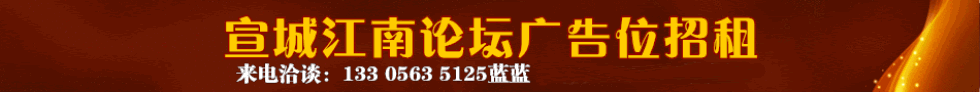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发表于 2023-8-2 21:27: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3-8-2 21:27: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安徽合肥
走进岁月(十三)
1970年春节,是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过的下乡后第二个春节。我们照例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到本公社各大队及至生产队;本生产队各家照例请我们去吃饭。至于吴秘书家,那更像是在自己家似的。
没过多久,已带着我两妹一弟由白湖农场先行回崇明老家乡下的妈妈来信说,身体不适,希望我能回去一下。
随后,我安顿好自己的事务,与女友及其奶奶同路回家。她们从镇江先下火车,我则前往上海。
在上海我姨妈家八九口人仅18平米的蜗居中挤住了几天,遂前往崇明。
那个时候,按上级安排,白湖农场拟将一部分干部及家属下放到阜阳地区亳县(今亳州)、涡阳县等地。而我妈妈及弟妹们回老家后成了没有户口(上海范围户口只出不进)的人。
那个年代,户口是所有人生活的重要保障。要是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所有计划供应的生活资料一概没有;即便生活在农村,也无下地干活挣工分从而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格。
面对如此窘境,让我进退两难。留下来,帮不上忙;回我下放地,他们怎么办?
见此,众亲戚、乡邻们主动对我们施以援手。除从物质上提供帮助外,经米新大队同意,我们家所属的米新五队还允许我这户口不在当地的人可参加本生产队集体劳动以挣得工分维持生计。
随后,亲朋好友们又鼓动我去找公社,看能否同意出具接收函,将我户口从安徽迁回老家?
按此建议,我前往向化公社,向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并提出请求。可在当时当地户口只出不进的政策下,此事根本无法成功。尽管去了多次,公社表示,忚们不能违背上级规定处理。对我们的处境除表同情外,实在爱寞能助。
鉴于此,我只能暂时静下心来,先为家人挣点饭吃再说,能挣多少是多少。
此后,拔秧、插秧、在棉田、玉米、黄豆地除草、施肥、浇水,或给棉苗打药水,割麦,割早稻,收黄豆,掰玉米等,全部参与。
当地还在部分稻田尝试过新的种稻方法。其时将稻种按规定横竖距离直接摆放在耙好的秧田里,每棵大约近十粒。这样省却了拔秧、插秧环节,既省时又省力。至于产量如何,我后来离开了,无从知晓,也没问过。
双抢期间,清晨两三点钟,人们即下田拔秧,天亮后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出工,中午稍事休息,下午继续,最忙时,晚饭后还必须出工。与我家同在五队的小舅舅及舅母常喊我去他家吃饭,尽管他有四个子女,条件很不好,还要负担我外婆,可他们仍倾尽全力帮助我们。
在拔秧或插秧期间,水田中时遇螃蟹或水蛇等。遇前者则大喜,凡遇后者的人,往往大喊我小舅舅的名字:宋鹤洲快来呀!于是我小舅舅飞跑过去捉拿(他会剥了蛇皮做二胡。其时用木杆作琴杆、竹筒作琴筒、细竹杆作弓、丝线作弓弦、两根粗细不同的棉线绕在麻将牌上在腌鸭蛋水里浸泡多时后分别作内外琴弦)。
夏日里,在给有的一人多高的棉苗整枝或一人多高的玉米除草、施肥或浇水时,闷热得气都透不出,浑身汗水不住从脸上、头上直流到鞋子里,衣裤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尤其是浇氨水时,那刺鼻呛人的气味更令人难以忍受。在路边大粪池里往田间挑沤好的肥料时,磨肩接踵的人群在小路或田间熙攘来往,煞是热闹。而割草头或用竹竿在河里捞水草,然后绞成长条埋于条播庄稼根部作肥料则是最开心的活计。人们口渴了,就一起就近到哪一家,拿起铜水勺舀起缸里的冷水(已用明矾澄清)咕嘟咕嘟猛喝一通。在田间除草时,若遇陌生人从近旁或不远处路过,做活很累的人们即可借机歇息一下,直盯着人家直至看不见才罢,也不顾对方是否觉得难为情?
做农活虽很苦累,但许多人在一起,边聊天边做事,却也减轻了不少疲劳,时间也很快过去了。
有时热很了,男孩们就跳进不远处灌溉用的横河(东西向)中游泳、戏耍一会。而当忙得不可开交时,最盼望的是到大队开社员大会或是下大雨,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好好休整一番。
若遇谁家盖房子,生产队所有劳动力全部出动,帮主人家用板车到窑厂拉回砖瓦。主人家则以烟、酒、饭让参与者尽情奢侈一回。
当地凡在河(东西向)沟(南北向,比河窄,仅宽5米左右)边,沿河岸都长满芦苇。夏秋时节,那密密匝匝覆滿河岸,类似北方青纱帐的芦苇如一堵堵高高的围墙般将多姿的田园景色围揽其中,人在河沟边行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芦苇可编箩筐、畚箕、簾子、芦蓆、扎成瓜或豆架子、过去农家编成厚实的芦笆作草房的墙壁、过去粮站露天粮囤用的囤条等。下脚料则被当作柴禾。如今因滥施除草剂,使得这一当地特色及众多副产品均被毁灭殆尽。
当地众多河沟形成密布的水网。过去通往长江的河口无水闸,夏日里只要涨潮或暴雨,平地总会形成水及小腿肚的一片泽国水乡。后来各河口有了水闸,原先为到近海撒籽然后迴游进长江及河沟的螃蟹们不再能自由出入小岛。于是它们就翻越江堤完成繁衍后代之重任。曾有集体挑江堤夜宿江边简易棚中的人,有人睡梦中突被腿上一阵剧痛刺醒。用手一摸,一只硕大的螃蟹被抓在手中。可能是找不到出口,故而向人类求助吧。
说到螃蟹,在我们家房子南墙不远处有一条小河,里面鱼、虾、蟹、蟛蜞(可吃)、骚蜞(只能沤作肥料)等众多(最后两者外形与蟹类似)水族。
我学着人家的样,用两根竹蔑交叉,撑起一尺见方小网的四角,将蚯蚓穿在铁丝上置于对角线位置,在竹蔑交叉处栓一草绳,草绳上端栓一芦苇做的三角浮子。这样的网具做上十几口。然后每隔五六米沉入河中。再用一根绑有树杈做的钩子的长竹竿来回起网。当网岀水时,感觉网上沉甸甸并有一青色大蟹出水时,其时心情如中了大奖一般。只见网中的蟹艰难地向网外爬行,可爪子穿进了网眼,很难行动。偶尔也有掉回水里或掉进棉花地里的。掉地里的蟹跑得飞快,我就得在棉花棵中艰难地与之追逐一番。那时镇上菜市螃蟹卖五角一斤,可自捉比购买,其趣味与开心程度无可比拟。
这样的日子过了八个月,到十月份,与我同插队的张同学来信说,庐江当地又开始招工、招生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随即动身,经上海姨妈家时,购了肥皂、白糖、糖果、糕点、塑料凉鞋、衬衣及假领子、当初答应帮人带的缝纫机梭芯、胶靯等当时极热门的上海货匆忙踏上了归程。
经镇江东郊女友家时仅住了一夜就又出发。实际共歇了两夜,第一夜是从镇江下火车后,才下午三四点就已无班车,只能找一小旅社住下。可小旅社也是床位紧张,通铺也剩最后一张,我只好与另一前往扬中的陌生男孩同挤一铺将就了一夜。
回到吴秘书家时,张阿姨把我好一顿埋怨,说是怎么也不该在老家待这么长时间!我无话可说。
后来她又多次在银岗大队徐书记面前说:二回有机会你一定要帮帮这两个小伢子。这让我们从心底感激万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