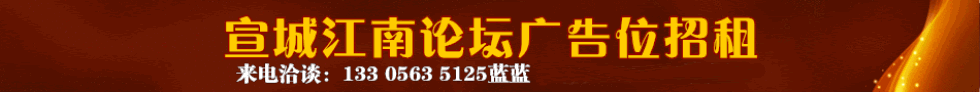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发表于 2023-12-6 18:47: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3-12-6 18:47: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安徽合肥
家乡的小河
从小到大,曾先后见过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等;在白湖时见过塘串河、马尾河等;到宣城后又先后见过誓节渡、水阳江、宛溪河、桃花潭、郎川河、青弋江及芜湖的清水河等。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还是令我梦牵魂绕的家乡那至多五米宽的曾经的小河。
家乡的小河,在我们家门朝东方向的老屋南边三十多米处,自西向东曲曲弯弯流过,东西两头分别与两条南北向泯沟(两头分别与东西向的较宽的横河连接,再与南北向更宽的竖河连接,竖河最后汇入长江。
每年春风吹起,小河两岸自水边直至岸上羊肠小道边会冒出密密匝匝的芦(苇)芽及茅草(可搓草绳)的细芽。这两种芽在春日里飞快向上。每逢一场春雨后,被杂草围拢的芽们每天傍晚都比早晨要窜高不少。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淀,此时小河里的水清澈见底,小鱼小虾们在其中嬉戏不停,有的虾子玩累了就呈垂直状紧附在没入水下的芦苇杆根部稍上处。此时若有人摘芦叶或扳芦杆闹出些许动静,那原本小憇的虾即飞快潜入水底,逃之夭夭。同时搅起一团混浊的泥沙,让人不知所踪。
那时的家庭主妇经常用破铜烂铁或鸡毛破布等在货郎担上交换针头线脑等小物件。小朋友们则对一分钱一颗的四角赤裸水果糖(当地用状如高粱的芦穄杆榨其甜汁制成)最感兴趣。那时能吃上一颗这样的糖块既属上乘又奢侈至极。
为了解馋,进入春季,小朋友们就会去沟边专拔那细长的茅草嫩尖芽,剥去外壳,借尝一下其中呈棉絮状的内芯所含的糖的甜味。
春天看得最多的是小河及房后南北向的泯沟里那一群群蝌蚪。它们甩动着细长的尾巴,在浅水处活泼地东游西逛,为即将成为青蛙做着准备。
小河边还长满小蒜(解放前后,北方南下的解放军拔生小蒜吃,当地人还嘲笑他们),人们用刀挑回后放入池中沤肥;还有的将已老的草头(黄花草)或河中的水草用两根竹竿绞起,再绞成长条埋在庄稼根部作肥料。
每年将至端午时,大人小孩都去河边摘芦叶准备包粽子。小河边的芦叶既宽又长,并且用芦叶包的粽子还特香。还有个重要特点,芦叶粽子到最后哪怕干硬得如同石头,却总是不坏。可见芦叶还极具保鲜作用。
进入夏季,河沟两岸一人多高的芦苇如长墙般将水面遮个严严实实。有时家人们在地里锄草,天太热,就扒开苇丛,在近岸浅水处放入一张小板凳,让我坐在上面,在双脚享受清凉的同时,借茂密的芦杆或叶子遮挡住炽热的阳光。
夏日的夜晚,最活跃的当数蚊子,特别是黄昏时,那恼人的嗡嗡声响成一片。乘凉时大人们边聊天边用芭蕉扇不停地为睡在饭桌或长凳上的小朋友驱离一波接一波前来叮咬的蚊群。其次,从河或沟里除了生出蚊子外,总会传来不断声的蛙鸣。在大人的庇护下,小孩子总能在蛙声中酣然入梦,直至凉透才被大人叫进屋睡觉。
当地盛产闻名遐迩的长江绒鳌蟹。过去不存在人工养殖,全是野生。蟹们先是翻过江堤到近海处产卵,卵成小蟹后再翻过江堤到淡水河沟里长成。七十年代时,菜市上螃蟹只售五角一斤。此外还有两种蟹状小动物,个头比蟹小得多。一种叫蟛蜞,另一种叫骚蜞。当地人将前者抓来后在石臼里冲成浆糊状,滤去渣滓,其汁水蒸熟后犹如蒸鸡蛋;后者味道怪异,不能吃。捉的人在傍晚将洋灯(一种四边各有-块防风玻璃固定在铁框内,上有顶盖和提把的煤油灯)放在沟沿苇丛边。那趋光的骚蜞们即自动向灯亮处围拢,于是只须悉数抓取放入竹笼中,回去后倒入茅坑中沤肥。
那时人们常用大大的四方攀网或固定在长竹篙根部的三角网网鱼或蟹、虾;有的则用三刺或四刺钢叉叉鱼;有的手持一如鸡罩般的竹笼,扒开苇丛,看准时机,将竹笼猛扣入近岸处浅水中,然后上身伏在笼上,以一手在笼内探摸可能被罩入的水货们;有的在淌水小沟筑一小坝,放上进口有倒刺,出口用布扎紧的竹笼,过一段时间,将竹笼提到岸上,解去出口处的布,往竹篮里一倒,必收获丰盛;有的用普通竹竿做鱼杆,以火烧缝衣针,弯曲后制成钓鱼钩,尖头虽无倒刺,却也能钓到鱼或虾或蟹或鳖;钓黑鱼则在大钩上绕上一团头发,并且让头发团在水中不停跳动,黑鱼属攻击性鱼类,见此情景,必来咬上一口,至此上钩;还有的摸鱼高手则空手在水中捉鱼或掏蟹洞或黄鳝洞等。当地有一盲人,却是摸鱼高手。
说到网蟹,最有趣的莫过于用那一尺见方的小方网,以两根蔑片交叉绑定,并将网的四角撑开,在其中一对角线位置固定一根细铁丝,穿上蚯蚓,在蔑片交叉处拴一草绳,草绳上端拴一芦杆弯成的三角浮子,一个网蟹器即告做成,这样的网做个十几口,在河边一字排开沉入水中,然后将一树枝杈作钩绑在一竹竿尽头,十几口网来回起一趟,至少会有五六只收入篓中。
夏季里的小河,发怒是常事。每次台风期间或暴雨后或涨潮时,河水总会漫上两岸,庄稼地顿成一片泽国汪洋。搭在河上的小木桥面也在水上东漂西荡。此时我的表舅就会与一群男孩子将桥面当木筏用竹杆撑着在水上疯玩一通。
我有时一个人伏在小河桥面上,双手扣住桥面一侧,双脚从另一侧垂入水中,开心地划拉几下享受河水赐予的清凉。有一次邻家李姓伯伯(他常在河中摸鱼捉蟹)坐在桥面上洗脚,我照例开始上述程序。不经意间,双手滑脱,身子往另一侧一坠。幸好伯伯在旁,将我抓住。若是那次仅我一人,又逢丰水时节,后果如何?不知道。
有一次我的小舅舅与几个男孩在河中撑着小衔泥船(疏浚河道用)玩,也让我坐在他们中间。不知怎么被我奶奶得知了,赶紧过来让我下船。不得已,我只好听从。接着她还要我马上回家,我不肯,她就追我。可她是小脚,跑不快,我在前面转着圈跑,她则边喊边追,连跑了几十圈也没追上,只好作罢。自此以后我发现,除了我奶奶,在同龄人中我也跑得比别人快,这也为我上学后爱好田径埋下了伏笔。
秋风吹起时,河沟边将枯的芦苇们,有节奏地向同一方向倾倒并直起,和着风声,汇成秋的交响。随着芦叶的渐次枯萎,健硕的芦杆依然挺拔。人们先是拔芦花扎成掸帚,再往后则将芦苇割下,好的用细绳串起做成晒物品的簾子,或编成厚厚的芦笆作草房的墙,或将芦杆压碎展开,编成箩、筐或畚箕,或编成一尺来宽长长的囤条卖给粮站作露天粮囤用。最后派不上用场的则与玉米稭、黄豆稭、高粱稭、棉花稭、油菜稭、小米或黄穄稭、大麦或小麦或荞麦稭、稻草(公社化以前水稻很少,但有一种旱稻)等统统作柴禾做饭用。
那时中国的钢铁工业落后。1958年大跃进时,社员们都在各生产队食堂吃饭,于是各类柴禾全部就地用来在河沟边的小高炉上焙烧各家收来的废铁炼铁用。最后烧出的铁坨坨什么用处也没有。
秋去冬来,田野里的各种谷物皆已归仓。只有围着一圈稻草绳的大白菜和冬小麦顽强地挺立在寒风中。
此时河沟边已无芦苇踪影,放眼望去,目力所及,十里冰封,百里朔气。自面前至地平线处,只有零散的大多为草顶芦笆墙的农家茅舍点缀其间,呈现一片肃杀之气。此时小河也进入宁静期。朔风中,水波不兴。逢低温,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好奇的小朋友们会小心翼翼地站上去试试冰面的承重效果。
河边的小路上同样结了一层冰,若不注意,走上去,冷不防会来个仰八叉。这还算好的,若是冰雪化冻,泥泞的路面根本无法行走,有人就在鞋子下面绑上木屐,以隔离鞋与路面接触,也便于行走。
冬日里的河水冰冷彻骨,为免冻手,人们洗菜时先将各类蔬菜切好,放进方底圆口的大或小竹篮中,在河水中猛淘几十下了事。
至于饮用水(七十年代以前,各家无水井),都用小木桶打上河水倒入缸中,再打上明矾澄清即可。
大约八十年代后,农村重新规划,新开了河道,各住家也集中到东西向的河边居住。我们家老屋搬迁了,原先的小河也被填了。特别是如今当地人用上了除草剂,芦苇也没了,原先沟边的绿色被驱赶怠尽,沟边一片光秃。如此场景,不知什么人看了会觉得舒服?
于是更激起我万分怀念那条伴我度过幼、童年时光且令我梦牵魂绕不止的曾经生机勃勃的可爱的家乡小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