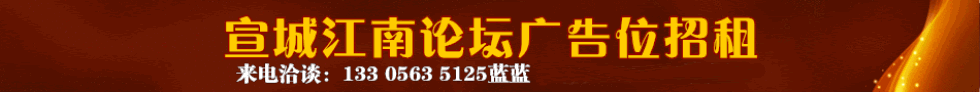|
|
 发表于 2023-12-4 20:25:4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3-12-4 20:25:4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安徽宣城
我的学校一一庐江梅山小学
1957年下半年,妈妈将我从老家带出,到我父亲上班所在地,白湖农场一大队。父亲原在华东军区医疗队。1950年,开始修淮河时,他们调至蚌埠一带的治淮委下属的劳改总队。治淮告一段落,劳改总队干部、犯人调至将开垦的白湖。
他们先在庐江盛桥与巢县沐集间的兆河上建了座水闸(该大队时称建闸大队)。然后南迁至白湖南畔,离梅山不远处的庐芜公路北侧一百米左右处成立白湖农场一大队。
妈妈带我到建闸大队时,父亲已随第一批人先行离开,我们正好随第二批人前往一大队。到一大队后,父亲即送我去梅山小学。
座落在梅山南边脚下的小学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第。大门对面是一个两层木楼。楼下左、右两边分別是教室和办公室。中间是中堂,后侧靠墙有楼梯上到二楼,左、右两侧分别是住宿生的女、男宿舍。
楼下两侧厢房也是教室。在东北角上是食堂。与其周边农家一样,这里长年飘出浓烈的腌菜的臭味。从食堂旁边后门出去是操场,竖有一副篮球架。再往东有一排平房,也是学校的教室。
第一天到校,看到教室里黑板仅架在两根木棍上,写字时不注意就会轰然倒下。桌、凳都是学生自带的,高低、长短不一,有的还是小方桌。我只能挤坐在别人凳头上,有时就站着。考试时到外面捡一块砖头,竖着摇晃不住地坐在上面。
报到那天上课时已是9月中旬,班主任兼语文宛老师告诉我,我是WO号(52),他浓重的庐江方言我没听懂,我觉得好像是16号。开始点名了,到16号时,我答:到。结果真正的16号也答:到。弄得我好难为情。于是心想,可能是26号,结果仍然不是。此时我已满脸通红。到36号还是错了,我的额头上、后背上已冒出汗珠。46号时再也不敢答“到”了。点到52号时,无人应答。老师说:你WO号。我才明白自己是第52号。后来想想当时怎么就那么傻?满满一教室的人,自己是开学多日后才从老家转来报到的,怎么也轮不到我是第16号或26号呀!
好在没过多久,期中考试,语文99(错了一个字),算术100,受到了班主任的表扬,这才挽回了点面子。
上学不久,1958年,白湖农场开始修筑东大圩。干部、部队带劳改在梅山采石用名叫歪歪车的小铁轨道车运石头。从我们住家出发不远,就有小铁轨。于是每当上下学途中,只要是劳改不在上班时间,我们就顺上坡推上庐无公路,下坡时人站在车踏板上,一路溜下直到梅山脚下或家门前。第一次溜,车下坡时,别人都跳上了踏板,而我还紧抓车帮,傻傻地跟着车跑。车速越来越快,人终被拖倒。幸好有一带工干部看到了,让同伴踩刹车。此时我的双膝已被枕木蹭得血肉模糊。
夏日午后上学时我们常下河或支渠洗澡。有一回大家从一停在河边的木船上往下跳,然后游向岸边。我那时不会游泳,也往下跳,当发觉脚踩不到河底时就慌了,连喝了几口水,同学赶紧从后面将我推向岸边。还有一次是我与另一同学在支渠洗澡。其时渠中有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我将其向宽约六七米宽的支渠对岸一推,准备再抓住它试图让木板将我带到对岸。谁知木板很快到了对岸,而我却到了渠中央。双脚踩不到底,随即双手乱抓、两脚乱蹬,喝了许多水,大约10秒时间,发觉踩到底了,也能正常呼吸了,终大难不死。
我从老家转来时是三年级。在老家用的课本是上教版,这里用的是人教版,我急得直哭。后来我借回同学课本,父亲请门诊室解质如医生为我用手抄了《语文》和《算术》。可惜1969年大水,搬家时未带出,被防汛的犯人当卷烟纸了。
到四年级,我发现同班一男同学每天利用课余写小楷。问他写什么?他说家里没钱,买不起书,只好借同学课本自己抄。此事对我触动很大。
学校的教导主任姓徐,带我们算术。每次上课前将作业做得好的本子先发给学生,不好的则上课时带进教室。然后依次翻开一本,先喊某学生站起来,接着斥责作业中的大量不是,且越说越气,最后边发火边将作业本撕成碎片揉作一团砸在那学生头上。
我的邻座是个19岁(三年级)名叫史广安的男生。有一天上课前,许多人正在教室门外疯。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徐主任指着我们说:来来来,进来考试!吓得小朋友们赶紧缩进教室。徐主任气呼呼地跑过来,指着那19岁男生大喊:叫你来考试,你躲什么家伙?过了一会,那同学闷闷不乐地回到教室座位上。开始上课了,徐主任拿着课本和卷子黑着脸走进来。还没开口,只见那19岁男生神情紧张,已是满头大汗。徐主任照例狠斥一通,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五道题还错了三道,你那个头脑只管切(吃)饭啊?
还有位张业培老师,带体育和音乐等。见我们许多男生除篮球外,对体育课其它项目都不感兴趣。就操着浓重的桐城口音说:腾同们哪,恩们不要以为干篮丘就是体入,不干篮丘就不是一一体入。此后我们经常学他说这话。
那时对学生惩罚最厉害的一项是降班。这比开除还难受。开除反正离开了,而从四年级降到三年级或从六年级降到五年级,与原班级同学早不见晚见,那种尴尬、难受劲旁人无法体会。
1957、1958年反右时,经常早上到校时听说某老师是右派被抓走了。有一回在大队听干部们说,你们那个校长(50多岁)打成右派被判劳改后,冬天挖湖泥,太冷,在淤泥里上不来,冻死了。
1958年,有一段时间一大队重盖住房,我们临时租住在梅山村。学校为让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农忙时除放农忙假外,有时干脆只是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回家参加劳动。
那时学校除有菜地让师生劳动锻练外,还常组织师生到生产队义务劳动。什么插秧、割稻、割麦、割油菜、积肥等力所能及的活都干过。
有一回是割油菜。我第一次使用锯镰刀(我们老家农村无这种刀),左手抓住一把菜杆,右手将镰刀对菜杆狠命一拉。只觉左手无名指一阵剧痛,抽出一看,血流如注。老师让我赶紧捂住回不远的家,然后到门诊室包扎。
1958年大跃进年代,每个生产队都开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由于粮食紧张,经常有农村同学没来上学,原因是有的农村生产队长早晨拦在路上,不让本队学生上学,说是你上午要是不干活就不给到食堂吃饭。有的学生只好下午再去学校。说是在食堂吃饭,实际只是在米粒可数的水里加大量菜叶填肚而已。
父亲在一大队上班,母亲带我住在那里。两个人每月总共三十多斤粮食,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为减少损耗,米都不淘而直接下锅。父亲从那时起直到六〇年以后,经常不吃早饭,为的是省下点粮食给我们。
学校老师同样很苦。他们常要农场学生为他们在农场食堂买菜。可那时能买到个青菜豆腐或韭菜炒鸡蛋就是上等的了。
有一农村同学带了稀饭到校。中午迟了一会到食堂去吃时,稀饭没了。他到处问,终于有个老师承认是他吃的。说是看那稀饭好厚(稠),比食堂的好多了,看到过了吃饭时间还在那里,我就把它吃了。后来他用食堂稀饭还给学生,那学生很不满意,说:尼大厚粥给他吃掉了。
校长占德明,有时给我们上语文课。他将倭寇读成矮寇,将铆钉枪读成柳钉枪。他要我们用做梦造句,我们都不知怎么造。他用浓重的桐城口音说:我昨晚做梦,吃得不错。连造句都离不了吃,那时生活多艰难可见一斑。
那时农场走读学生都从家带饭菜到学校,由食堂代蒸。刚开始一分钱可买4个牌子蒸四次,后来变两次,再后来变一次。食堂炊事员听说我父亲是医生,就要我带点橡皮膏给他,从此以后我就不用再买蒸饭牌子了。有一回一个农场学生带的红烧肉,但他不喜欢吃,就将肉甩在地上,几个因回家没饭吃而看我们吃饭的农村同学中的一个,把肉捡起来直接就放嘴里了。
看我们吃饭的同学中有一个与我同班。我就把他喊到我们自己教室,关上门,将我的饭拨一些在多层铝饭盒的小盘子里,用铅笔或树枝作筷子让他吃。为怕别人看见,他躲在课桌下,三两口吃完了再举起小盘要。如是两三次,原本一个人吃的饭被两个正是能吃之时的男孩一下就吃光了。后来我对妈妈说起此事,她就让我多带些。那同学无以为报,就带了些腌菜给我。
我的同班同学张宏伟与其低年级的妹妹每天用一外面被煤烟熏得乌黑的约18公分外面再包上白纱布以便提携的小铝饭锅带一角钱的饭(白湖农场饭票,一角二分一斤)。吃饭时,哥哥用筷子在饭锅里将饭一划为二,多的6分,少的4分。他说他是哥哥,人大些,吃6分的。有时他不急于吃,说是将饭做成发糕再吃,他妹妹只好等着。他将纱布摊在课桌上,将饭倒上,包起来,与另一同学两人各抓凳脚朝上的板凳,用凳面狠砸饭包,待饭被砸成饼,再与其妹妹分食。
还有一对兄弟,分别在三和一年级。两人用一大搪瓷碗带饭。吃饭时,哥哥拿着大碗只顾自己吃。弟弟拿着小碗看。忍无可忍之时,只见机灵的弟弟,看准哥哥扒一大口饭后将碗稍放低之时,猛然跃起,用自己的小碗在哥哥的大碗里刮出半碗或小半碗饭来充填自己的肚子。
那个物质资料匮乏的年代,铸就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今想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有一次早上,我有点不舒服。我爸爸就说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可我妈妈用棍子把我赶出家门。走到梅山北侧山脚,路旁有一生产队带顶棚的大积肥池。为报复我妈妈,我走了进去。中午放学的队伍来了,我混入他们当中回家。后来有同学看出来了,就告诉了我妈妈。我被打了一顿。
有一个深秋下午,放学时天已擦黑,又下起了濛濛细雨。我一个人走在往一大队一中队的土埂路上。偶尔回头一看,暗乎乎的夜色里,也有一人在急急地走路。不知他是劳改还是别的什么人,我很害怕,只好半小跑向前。回到家身上又是雨水又是汗水,头昏昏沉沉,难受极了。
在梅小时,我们家所在一大队一位曹姓会计经人介绍与杨柳公社梅山大队的宛凤花谈起了恋爱。他常写信让我带给那正上五年级的对象。我估计那女孩当时至少已20上下了,后来他们终成眷属。不过孩子出生不久,听孩子外婆向一大队干部家属诉苦:说是他女婿心好狠,小啊晚上哭,他说把小啊甩床底哈Ke,说着还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初在梅小读完四年级,我们还步行数里到杭头小学参加毕业考试,过后还发一张初小毕业证书。
1960年下半年,白湖农场首办干部子弟学校,于是在当地农村小学上学的一至五年级的白湖子女全部被转入农场学校。我所在的这一届升入六年级,成为白湖学校的首届高小毕业班。 |
|